

前言
近年来,洗钱犯罪手段不断翻新,从传统的银行转账、虚假贸易到虚拟货币、口令红包等新型方式,洗钱行为日益隐蔽化、复杂化。洗钱犯罪不仅破坏金融管理秩序,还为贪污受贿、电信诈骗、非法集资、涉黑犯罪等上游犯罪提供资金“漂白”渠道,严重危害社会经济安全。
为增强公众对洗钱犯罪的认知,司法机关近期发布了多起典型案例,涉及受贿、虚拟货币、涉黑资金、电信诈骗等多种洗钱手段。本期小编通过深入剖析这些案例,揭示洗钱犯罪的运作模式、社会危害及法律后果,并提供实用的防范建议,帮助大家识别风险,远离洗钱陷阱。
案例一:以投资形式实施"自洗钱",掩盖受贿所得
案情回顾
2017年至2023年,某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范某利用其主管工程项目审批的职务便利,通过违规干预招投标程序、为特定企业谋取不正当利益等方式,先后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2000余万元。为规避司法侦查,范某于2022年2月采取多步骤、多环节的隐蔽操作,将其中262万元现金分四次交予朋友林某,并以林某名义在某商业银行开设账户。
随后,这笔资金被伪装成"购房款",通过银行转账方式转入某房地产开发公司账户。为完成资金"合法化",范某通过其孙女名义购置房产,并办理不动产登记。整个过程形成完整的资金闭环:受贿所得→现金交付→他人账户中转→虚构交易→资产转化。值得注意的是,范某在操作过程中刻意选择非亲属关系的第三方账户,以切断资金流向与本人的直接关联。
法律定性
范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与洗钱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1条,洗钱罪明确将"贪污贿赂犯罪"纳入上游犯罪范畴,规定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行为予以刑事处罚。
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重大修订,标志着"自洗钱"行为的独立入刑。此前,司法实践中存在"洗钱行为依附于上游犯罪"的认定惯例,但修正案明确规定:即使上游犯罪与洗钱行为由同一主体实施,仍可单独构成洗钱罪。这一修订体现了国家对金融安全与反腐败治理的双重重视,为打击"自洗钱"提供了明确法律依据。
判决结果
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范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其受贿行为严重损害职务廉洁性,洗钱行为则进一步破坏金融监管秩序。最终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150万元。判决书特别指出,范某"主观恶性深、社会危害大",其行为已构成对司法权威的系统性挑战。
洗钱手法分析
范某选择现金交付而非银行转账,旨在规避金融监管系统的资金追踪。通过借用林某成账户,范某构建了"资金中转站"。此类操作通常涉及伪造身份证明文件、虚构交易背景等手段。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统计,2020-2023年间,因账户借用导致的洗钱案件占比达37%,凸显"实名制账户"管理的重要性。
案例二:利用虚拟货币非法集资、洗钱
案情回顾:虚拟货币骗局的精心布局
2020年4月至12月,王某某等人策划并实施了一起以虚拟货币为载体的非法集资案件。他们虚构名为“GUCS”的虚拟币,通过伪造技术白皮书、伪造交易所资质文件等手段,构建虚假的项目背景。该币种被刻意包装为“与比特币同等价值”的创新资产,甚至通过雇佣“水军”在社交媒体、投资论坛中散布虚假利好消息,营造“技术领先、收益稳定”的假象。
在具体操作中,王某某团队采用“多层分销”模式,以高额返佣激励现有投资者发展下线。据调查,部分参与者因短期获利而盲目扩大投资,甚至将房产、积蓄投入其中。为掩盖非法目的,团队通过虚假交易制造市场活跃假象,操纵“GUCS”价格在短时间内暴涨300%,诱使2.9万余名投资者购入,最终导致17亿元人民币的巨额损失。
2020年10月,王某某将诈骗所得的2.49亿元“泰达币”(USDT)转移至境外。马某明知资金来源非法,仍通过境外外汇平台进行“币种转换”,将虚拟货币转化为法币后再分批转入多个银行账户,累计转移资金9000余万元。此外,马某还协助另一名犯罪分子谢某某将“泰达币”兑换为人民币,通过其妻子账户完成资金归集。这种“多层嵌套”的操作模式,显著增加了资金追踪难度。
法律定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王某某等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非法集资,且数额特别巨大,构成集资诈骗罪。而马某在明知资金系犯罪所得的情况下,仍协助转移、转换资产,符合《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
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犯罪团伙利用虚拟货币的匿名性、跨境性特点,形成“非法集资—资金洗白—资产隐匿”的完整链条,凸显了新型金融犯罪的技术复杂性。
判决结果
法院综合考量犯罪情节与社会危害性,对主犯王某某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马某因洗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50万元;其他涉案人员根据参与程度,分别被判处15年至3年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及罚金。
洗钱手法分析
1.虚拟货币的匿名性陷阱
虚拟货币的分布式账本技术虽具有透明性,但其地址匿名性为犯罪分子提供了“遮蔽面”。本案中,王某某团队通过多层级钱包地址转移资金,使监管机构难以追溯原始来源。
2.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盲区
马某利用境外交易平台的“监管宽松”环境,将虚拟货币转换为法币后通过离岸账户转移,规避了国内反洗钱监测系统的实时预警。
3.多层账户的“迷雾战术”
资金经由多个关联账户反复划转,形成复杂的资金路径。例如,部分资金通过“空壳公司”账户中转,进一步混淆资金流向。
本案警示我们,虚拟货币的“技术红利”可能成为犯罪工具,而公众的“认知盲区”则可能成为犯罪温床。全社会需共同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唯有通过法律约束、技术监管与公众教育的多维联动,方能有效遏制洗钱犯罪,守护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
案例三:亲友协助"漂白"涉黑资金构成洗钱罪
案件背景与社会危害性分析
2019年6月,一起涉黑洗钱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该案涉及某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盘踞当地,通过非法放贷、暴力催收、垄断经营等手段获取巨额非法收益。据检察机关指控,该组织在2015年至2018年间,累计非法获利逾2.3亿元,严重破坏当地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作为核心成员陆某某的妻子,何某某在明知其丈夫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前提下,仍主动实施资金转移行为,其行为不仅助长了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更对司法机关追查犯罪事实形成阻碍。
犯罪行为的系统性特征
1.资金保管的隐蔽性
何某某在陆某某潜逃期间,将60万元犯罪所得收益存入其个人账户。根据银行交易记录显示,该笔资金通过三次跨行转账完成,首次存入时采用"零钱存取"方式规避大额交易监控,后续转账均通过ATM机操作。这种分段式资金流转模式,符合《刑法》第191条关于"通过资金交易、转移、转换等方式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典型特征。
2.投资行为的伪装性
经法院查明,何某某将涉案资金转入其亲属名下的建筑工程公司账户后,以"项目投资"名义用于某房地产开发项目。审计报告显示,该笔资金在项目中实际占比不足3%,且通过虚构工程合同、虚开发票等手段进行账目处理。这种"资金混同"操作,既符合《反洗钱法》第16条规定的"通过投资经营等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也体现出犯罪分子对金融监管体系的深度研究。
最终判决采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8万元。本案的审结不仅展现了司法机关打击黑恶势力经济基础的坚定决心,更揭示了洗钱犯罪的复杂性与隐蔽性。随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实施,洗钱罪的犯罪主体已从"特定主体"扩展至"任何自然人和单位",这要求社会各界切实增强法律意识,共同筑牢反洗钱的人民防线。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应时刻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的警示,避免因贪图小利而触碰法律红线。
案例四:为犯罪分子提供个人信息,为洗钱行为提供掩护,需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2月,上海市浦东新区发生一起因个人金融信息泄露引发的洗钱案件。被告人郑某某(男,32岁,某科技公司职员)在利益驱使下,主动向犯罪分子提供本人身份信息及金融账户,协助完成非法资金转移,最终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追究法律责任。该案不仅揭示了当前网络犯罪链条中个人信息滥用的严重性,也凸显了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
案情回顾
据检察机关调查,郑某某在2023年12月通过社交平台结识一名自称"兼职代理"的犯罪嫌疑人。对方以"月入万元"为诱饵,承诺提供"轻松赚钱"的机会。郑某某起初存有疑虑,但在对方出示"营业执照"及"佣金结算凭证"后,逐渐放松警惕。此后,该犯罪团伙通过加密通讯软件与郑某某频繁联系,要求其提供身份证原件、实名认证的银行卡及绑定手机号码,并指导其下载某第三方支付平台APP,注册商户账户。
为规避监管,犯罪分子向郑某某传授"操作技巧":通过伪造交易流水、虚构商品名称等方式,将非法资金伪装成正常商业往来。郑某某在明知账户可能被用于非法用途的情况下,仍按指示完成账户绑定,生成收款二维码。据统计,2024年2月1日至15日期间,郑某某通过该账户累计完成27笔转账操作,单笔金额从500元至8000元不等,累计转移涉案资金15000余元。作为回报,郑某某先后收取"劳务费"800元。
法律后果与司法处理
案件侦破后,公安机关依法对郑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经审查,郑某某的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规定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考虑到其犯罪情节较轻,且主动交代犯罪事实、退缴违法所得,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二款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但根据"行刑反向衔接"工作机制,案件材料被移送至民事与行政检察部门,推动行政处罚程序启动。
2024年3月,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对郑某某处以10日行政拘留并处1000元罚款,同时追缴其违法所得800元。值得注意的是,该处罚决定书特别注明:"本案系典型的信息网络犯罪关联行为,行为人虽未直接参与诈骗,但其提供的金融账户已成为犯罪资金流转的关键环节。"
法律警示
本案引发的法律思考具有广泛现实意义。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银行账户、支付账户。郑某某的行为直接违反该规定,为其后续法律责任埋下伏笔。其次,该案揭示了当前网络犯罪的新型特征:犯罪团伙通过"技术外包"模式,将资金流转环节分散至大量普通公民账户,形成隐蔽的犯罪网络。
专家指出,此类案件频发与公众金融安全意识薄弱密切相关。据统计,2023年全国公安机关破获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涉及非法账户使用的占比达67%,其中约43%的涉案账户由"不知情"的公民提供。这要求金融机构强化账户开立审核,同时呼吁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本案的处理体现了我国对网络犯罪"全链条打击"的司法政策。从刑事追责到行政处罚,从追缴违法所得到开展法治教育,形成了完整的责任追究体系。同时,该案也警示公众:在数字经济时代,每一个看似普通的金融操作都可能成为犯罪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公民必须增强法律意识,切实履行个人信息保护义务。
END
转载来源:光证普法微信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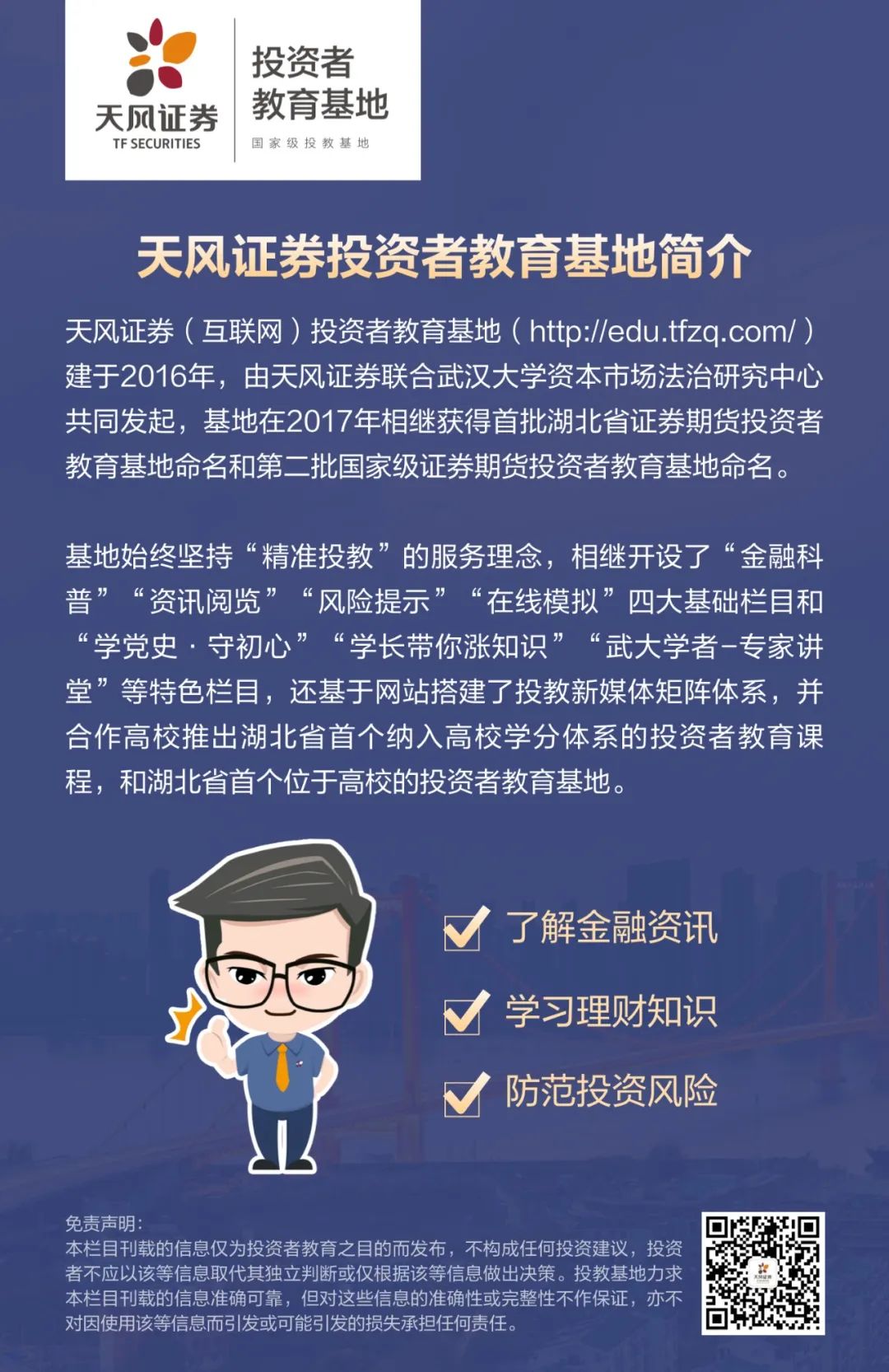
- 中国结算投教 | 北交所存量上市公司代码切换(上期)
- 中国结算投教 | 北交所存量上市公司代码切换(下期)
- 中国结算投教 |《关于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若干意见》深入推进证券期货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
- 中国结算投教 | 保障金融权益 助力美好生活 证券账户查询03
- 中国结算投教 | 保障金融权益 助力美好生活 小额遗产继承非交易过户04
- 中国结算投教 | 投资者保护典型案例之证监会上海证监局指导上海市证券同业公会推动优化小额遗产继承手续
- 中国结算投教 | 投资者保护典型案例之全国首创警证联合反诈劝阻机制证监投教专业力量参与公安投资理财类诈骗劝阻
- 中国结算投教 | 投资者保护典型案例之重庆证监局联合检察机关等各方共建证券犯罪警示教育中心









